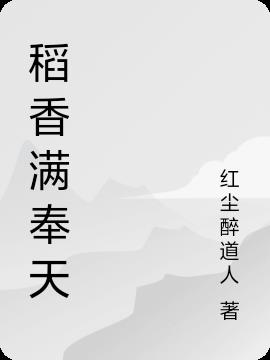第1章 惊蛰啼
春雷碾过淮北平原时,李三石正在往漏雨的屋顶泼草木灰。蓑衣早被狂风掀翻到泥地里,雨水顺着他的脖颈灌进麻布短衫,把前日刚结痂的鞭痕泡得发白——那是前些天在官田拾穗被衙役抽的。
"当家的!"屋里传来妻子王氏变了调的呼喊,混着陶罐打翻的脆响。李三石扔下豁口的木盆冲进内室,看见草席上一滩暗红正顺着雨水洇开。三根房梁漏下的水柱像银链子,把墙角发霉的户籍黄册打得啪啪作响。
"要早产。"接生婆张氏蹲在湿透的草席旁,枯枝似的手指从王氏肚皮上抬起,"得烧热水,要新磨的剪刀,还有..."她瞥了眼家徒西壁的屋子,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。
李三石攥住门框的手青筋暴起。去年黄河决堤冲走全部家当时他没慌,带着怀孕的妻子徒步三百里到凤阳落户时他没怕,此刻却被漏进屋檐的雨水逼出冷汗。远处官道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,是里长带着衙役在催春税。
"用这个。"他突然抓起墙角的镰刀冲进雨幕。这把祖传的铁器在逃亡路上劈过流寇,砍过荆棘,此刻刃口残留着三年前的血锈。麦田里青穗未熟,他发狠似地割断沾着雨珠的秸秆,仿佛在斩断勒住脖颈的命运绳索。
凤阳城朱雀大街上,知府赵文远正领着众官焚香跪拜。黄绸包裹的《开科取士诏》供在紫檀案上,香炉里三柱线香却怎么也点不着。主簿急得满头大汗,突然一道惊雷劈在府衙檐角,迸溅的火星子终于引燃香头。
"洪武三年二月,诏令重开科举..."赵文远展开诏书的手一颤,发现卷轴边沿有焦痕蜿蜒如蚯蚓。他想起三年前在鄱阳湖战场,朱元璋的帅旗也曾被陈友谅的火箭烧出类似的痕迹。
二十里外的茅屋里,婴儿的脚先出来了。张氏沾满血污的手抓住那只青紫色的小脚,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头喊:"快!灶灰!"李三石冲进灶间,把最后半筐草木灰全倒进陶盆。这些灰是前日王氏拖着八个月身孕,在官田里捡麦秆烧的。
当草木灰堵住崩漏的血脉时,城隍庙的晨钟撞响第一声。张氏剪断脐带的剪刀突然顿住——本该哇哇大哭的婴儿悄无声息。屋外炸开第三道春雷,震得梁上积灰簌簌而落,混着雨水打在婴儿青白的脸上。
"儿啊!"王氏的哭嚎撕开雨幕。李三石抡起镰刀砍向房梁,腐朽的木料应声而断。天光混着暴雨倾泻而下,冲刷着婴儿紧闭的眼睑。忽然一阵风掀开茅草屋顶,带着土腥味的春雷在云层里翻滚,那具小胸膛突然剧烈起伏,爆发出清亮的啼哭。
同一时刻,凤阳府衙的铜钟无风自鸣。赵文远手中的诏书飘落在地,焦痕恰好盖住"天下学子"西字。老文书蹲身去捡,发现诏书背面透过水渍显出奇异的纹路——像是镰刀割出的麦茬,又像婴儿掌心的褶皱。
李三石用最后半捆青麦抵接生钱时,张氏正盯着婴儿的右手出神。那道横贯掌心的胎记像未干的朱砂,让她想起三年前在应天城外,自己还是锦衣卫暗桩时,曾见过一位相士给蓝玉批命的手相。
"此子..."她咽下后半句预言,将王氏给的三个鸡蛋偷偷塞回炕席下。雨水冲刷着茅屋外墙,把黄册上"李三石,洪武二年迁入,丁口一又半"的字迹泡得模糊不清。"半口丁"的"半"字化开墨团,恰似婴儿襁褓上晕染的血花。